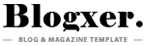痖弦:每个文人都应该是“广义的左派”
●他师从张彻、齐如山,演过孙中山,获最佳男演员金鼎奖。
●三十多年来,台湾一共选了三次“十大诗人”,他每一次都当选。
●他曾任《联合报》副总编辑,提倡“副刊学”,把副刊提高到学问的层次。
大家访谈【文化老人系列】
痖弦小传
痖弦:原名王庆麟,1932年生于河南南阳。复兴岗学院影剧系学士,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。与张默和洛夫创立“创世纪诗社”,发行《创世纪》诗刊,号称诗坛“铁三角”。曾任《幼狮文艺》主编、《联合报》副总编辑。著有《痖弦诗集》、《中国新诗研究》、《弦外之音》等。
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2007年驻校作家邀请了痖弦。三十多年来,台湾一共选了三次“十大诗人”,痖弦每一次都当选。这对于一个几十年没有写诗的诗人来说,可谓奇迹。
痖弦常说:“一日诗人,一世诗人”。在他看来:“诗是很不容易戒掉的瘾,诗是一种癖性,一种毛病,喜欢上诗,就不容易抛掉它。严肃地说,诗也是一种信仰,宗教家可以以身殉道,诗人可以以身殉美,诗人是一辈子的诗人,诗人的努力是一辈子的努力,诗人的最高完成也就是诗的完成。”今天,痖弦依然是《创世纪》诗刊的发行人,这份诗刊已经发行超过半个世纪了,也是一个奇迹。白先勇形容《创世纪》诗刊是九命猫,永远死不掉。
痖弦健谈,语言风趣,神态憨厚。他说:“我就是台湾的一个盗火者,从《创世纪》诗刊开始,就开放了30年代的东西。”他曾开启了台湾读者认识中国文学的另一扇窗户,在他编辑的报刊上“开放”了鲁迅等作家的作品。闲谈中,痖弦讲了晚年成为台湾文化重镇的胡适、钱穆、林语堂、梁实秋的许多逸事。他笑道:“胡适每一个单项都很薄弱,但是加在一起就很伟大。”
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,诗人的身份早受公认,他更看重要的是编辑事业:“我那时候是写了几首诗,是经得起时间的淘洗。现在评我的诗的文章很多,我觉得很感念。我宁可说我是一个成功的编辑。我对编辑非常着迷,非常醉心,我把编辑的意义看得很庄严,我不太喜欢人家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,我认为编辑就是一种事业,简直就是一种伟业。所以在编辑上我花的工夫很大。我在文学上耽搁了一些事情,我也无怨无悔。千万不要把编辑当成是为人作嫁衣裳,尽量地做好,那东西跟你自己写文章的意义是一样的,甚至意义更大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一首诗,在世界上的影响,老实讲很渺茫,但是如果一个副刊一纸风行的话,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。或者说,由你培养很多年轻作家,一个大时代就起来了。”
从《联合报》退休后,痖弦在加拿大与台湾两边生活。他依然关注报界发展:“现在由于电脑的出现,也有一些不好的报纸到台湾去竞争,台湾善良的文化品位都在降落,整个副刊的时代有点过去了,报纸的时代也过去了。所以现在大家提起来,就认为我们编副刊的时代是报纸的黄金时代。”
不是投笔从戎,是胃在燃烧
痖弦原名王庆麟,1932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县。1948年,随就读的南阳中学离乡,与父母永诀,颠沛流亡数千里,由河南到湖北再到湖南,入湖南衡阳国立豫衡中学。1949年,在湖南零陵从军,随部队由广州到台湾。
南方都市报:离开家乡南阳时,你16岁,了解天下的大势吗?
痖弦:不了解,尤其是乡村青年。一出来,不是很理性地了解天下大势。老师带我们出来,我们家长也觉得跟着老师不会错,就走了。小孩子也不知道离开是多严重。家里人去送我,我还不耐烦,好像去远足一样。父母去送我的时候,觉得爸爸妈妈土土的。我妈妈给我煎了油饼,放在我背包上,我还凶她:“干什么吗?”回头就走了,不晓得就是永诀。到了42年后我再回到大陆,他们都过世了。小孩子时代不觉得悲伤,到中年以后越想越惨!
南方都市报:1949年你怎么去当兵?
痖弦:我们好几天都没有吃饱饭,已经陷入半饥饿状态。我们如丧家之犬,看到告示:“有血性、有志气的青年到台湾去!!!”仔细一看,说是去台湾三个月,给少尉军衔。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台湾在哪里。已经走投无路了,进去看看吧。出来一个人,说河南话,我们农村青年最相信老乡,只要是老乡,就不会是坏人。那个人说:“报名不报名没关系,吃饭啦。”就煮了一锅肉给我们吃。我们至少有一年没有吃过肉了,吃了肉以后就不好意思,你看我,我看你,就报了名。人家写自传,可能会说投笔从戎,我说:“不是我的热血在燃烧,是我的胃在燃烧。”(笑)那时候招兵站的人说: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,去了每个人要发一条美国军毯,发一件软玻璃的雨衣。一个礼拜以后,从零陵坐火车到了广州,从广州坐船到台湾去,那是1949年8月初。
南方都市报:在广州时有什么见闻?
痖弦:我们在广州时住在孔庙里,番禺中学的原址就是孔庙的一部分,改成学校了,离中山公园不远。我们在广州呆了个把礼拜,每天在街上走,我们到中山公园去看相,乡下人没有看过相,到水上体育会去游泳。军人去看电影不用钱,我们第一次去看电影,不习惯:怎么人脸一下变大,一下变小?那时候还不知道特写这个东西。那正是夏天,就觉得广州人很奇怪,这么热的天,还吃一种东西放在嘴巴里烫着就拿出来,还冒烟,不知道是冰棍。这几天在广州跑一跑,就到台湾了。
只演一部戏即获最佳男演员
痖弦在台湾当了4年兵后,1953年考取复兴岗学院影剧系第二期,受到老师李曼瑰鼓励,开始创作剧本并写诗,获全校新诗比赛首奖。多年后,痖弦在纪念国父百年诞辰话剧中饰演孙文,获1965年最佳男演员金鼎奖。
南方都市报:为什么去上复兴岗学院影剧系?
痖弦: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政治性的学校,其实里面的师资差不多跟一般的大学一样整齐,有音乐系、美术系、影剧系、新闻系、中文系、外文系。我一个小兵,在失学的年代,能够念到那个学校,是很值得珍惜的。而且后来我们开窍,也是那些老师的带领,包括李曼瑰、齐如山、张彻。
南方都市报:张彻上课什么样的?
痖弦:张彻每天抽烟,牙都熏黑了,他说:我去教书可以,我要在课堂上抽烟。一边抽烟一边讲课。上课就是随口地讲,讲抗战的时候演戏,怎么编剧,因为他抗战的时候已经有名了。讲他对诗的感受,诗与戏剧之间的关系。张彻原来写新诗的,得过中华文艺奖金。后来他到香港做出了一番事业,他拍武侠电影,像《独臂刀》这些,运用了大量的男性演员,对香港电影贡献很大,他和胡金铨在武侠电影的成就很大,把电影美学的品质提高了。
南方都市报:他的文章写得好,字也写得不错。
痖弦:他是个天才。他回台湾,都是我招待他。我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了,所以张老师每年回来都找我。他知道我写新诗,很高兴。
南方都市报:齐如山的著作这几年在大陆出版了很多。
痖弦:齐如山讲京剧。他是一个支持梅兰芳的人。他写北京的老市井写得很好,但在台湾没有整理过他的东西,现在大陆倒是通通整理出来。他死得也比较早,死时大概台湾出版业还不太发达。
南方都市报:他上课怎么样?
痖弦:我们不太听得懂他讲话,声音很小,他还用老词,第一句话就讲“诸君”,不讲“各位同学”。他讲梅兰芳的戏,京剧怎么样在徽班进京以后,吸收了各地的精华,京剧完成的时候并不是很早,一直到现在保持生命力,就因为形成比较晚。
南方都市报:你那时候对戏剧感兴趣吗?
痖弦:非常感兴趣。后来我不觉得我能演戏,因为脸上没有什么线条,反应也比较迟钝。我那时候已经喜欢诗了,但是觉得戏剧方面不能交白卷啊。所以我就转向中国戏剧史的研究,从宋元戏曲到话剧,后来我到我的母系去教书,我的兴趣就向诗慢慢发展。但是戏剧对我影响很大,所以我写诗都受到戏剧的影响,余光中就讲我的诗是“戏剧的诗”。
南方都市报:后来你演了孙中山,还得了最佳男演员金鼎奖?
痖弦:这是我唯一演的一部戏。1965年,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,台湾要演戏,希望找一个生面孔,是受过舞台训练的,就找了我,我演孙中山,演了70多场。我后来拿了一个最佳男演员,对我讲是一个插曲,我也是很认真地演。不过,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代,戏里也没有什么女角,宋庆龄也没有出现。孙中山一出来就是长篇的演讲,所以戏很枯燥无味,但是当时大家很重视。大概除了蒋介石没看,其他人都看了。后来我就到美国爱荷华去了两年,回来蒋经国召见我,他在里边办公,有一个秘书坐他外边,秘书我认识,我说:“你要给我介绍一下,我才能去看他嘛。”“他认识你,不必了,他听过你‘训话’的。”(笑)他看过《孙中山》,孙中山一出来就训话,可见他也看过。孙科夫妇也去看了,看了还流泪,我想流泪不是因为我的演技吧,可能是想到他父亲的革命事业等等。后来散戏的时候,他们到后台给演员打招呼,那时候我还没有卸妆,孙科是考试院院长,我当然让他站中间嘛,他让我站中间,因为我还没有卸妆,理论上我还是孙中山,他们夫妇围着我,照了一张相。
雪夜看禁书是人生一乐
1953年10月,痖弦参加中华文艺函授学校学习,师从覃子豪等人,以“痖弦”为笔名在纪弦主编的《现代诗》季刊发表第一首诗《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》。1954年,从复兴岗学院毕业,调任左营军中广播电台编辑兼外勤记者。结识张默、洛夫,共同创办《创世纪》诗刊,该刊办了五十余年,至今仍在出刊。
南方都市报:从50年代起,台湾新诗的兴起在新文学史中是一段有意思的历史,你如何关注新诗的发展?
痖弦:新诗很有意思,一开始是同北大有关系的,胡适发起的。文学的形式常常是起自民间,然后为知识分子所重视,再做艺术的加工,成为一个正式的文类。规律都是这样,弄得太精致了就死掉,然后再一个民间形式出现。但新诗不是来自民间,是来自学院,因为“五四”这一步跨得太猛,学院的人当然支持新文学,但是还有很多老古板觉得这东西没有太多道理。
新诗原来是在学院,后来完全是挤到民间来了,就变成中学生特别有兴趣,文艺青年特别有兴趣。本来它是在朝的,后来变成在野了。在野的情况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,后来中文系的教育并没有全面地接受新文学,关于小学这部分,训诂、考据还是很严格。老先生们不太承认新诗的,认为白话文运动里成就最差的是新诗,认为新诗还没定型,说了好多年。所以我们当时是进不了学校的,有很长一段时间,中文系不谈新诗的。假如说,班上有学生喜欢写新诗,老师也觉得这个学生怪怪的,在大学里不好好做学问,写什么新诗呢?一般人认为谁生日送个新诗是不庄重的,要写一个旧诗才正式。一直到最近20年,新诗才进到学校里去。现在新诗又好像从在野又变成在朝了。
南方都市报: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新诗?
痖弦:我在复兴岗学院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新诗,也参加学校的新诗比赛。后来,我就在纪弦先生的《现代诗》杂志发表一篇东西,对我鼓励很大,那诗是《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》,这是我正式的第一首诗发表。那时候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,写诗得到的稿费还不够寄一封挂号信。怎么办呢?就用一封平信,里面装几个邮票,代稿费。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到香港来投稿,香港稿费高。我的第一本诗集是香港《学生周报》主编黄崖推荐到香港国际图书公司出版的,所以我到香港来,就开玩笑说:“我也是香港作家。”小思是“资料大王”,她就知道我讲的意思。
南方都市报:《创世纪》诗刊是怎么办起来的?
痖弦:《创世纪》诗刊是张默、洛夫和我办起来的。洛夫是复兴岗学院第一期毕业的,我见到他们的时候,《创世纪》诗刊第一期已经出来了,我从第二期开始参加“创世纪”。洛夫比我大4岁,张默比我大2岁,小孩子时代,大几岁就知道更多的事情了,所以他们两个主要在设计这个刊物。一直到现在,我还是这个杂志的发行人。
那时候我和洛夫两个人在左营军中电台做编辑,事情不多,每天写诗。那时候播音的人跟写稿的人是两套人马,我们是写,不播。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宿舍里面,有时候头对头,有时候脚对脚,每天在写诗,很多诗都是那时候写成的。那时候二十岁出头,现在年轻人是“飙车”,我们那时候是“飙诗”。(大笑)小朋友之间也有轻微的比赛,忌妒的心理,洛夫写一首,我一定要还他一首。相激相荡,很有收获。
南方都市报:在唐代,李杜、元白似乎也是这样的。
痖弦:后来商禽到左营去,他是宪兵,常常到我们那儿转,他看了不少的禁书。
南方都市报:那时候什么样的书是禁书?
痖弦:30年代的书算禁书,绝对不能看,看了很严重的。大概只有冰心、徐志摩、朱自清是可以看的,即使没有问题,人在大陆也不能看,万一他出问题,你负责?所以商禽来了以后就开始给我们看他的手抄本。那时候很重要,雪夜看禁书是人生一乐也。
南方都市报:你都看了什么禁书?
痖弦:几乎全部的鲁迅作品当时都是查禁的,郭沫若、左翼文学的作家。这个禁书借给你,是真正有交情才借给你的,否则你打一个小报告,我完蛋了。有时候一篇文章喜欢,整个抄下来,有时候一本喜欢,一本都抄下来,有时候上面有插图,手抄本也画个插图。就像中世纪的僧侣抄经一样,抄一遍,永远不会忘。后来我们之所以有一点基础,跟那个事件很有关系。禁书,对你的感染力特别强,有偷吃禁果的感觉,像盗火者普罗米修斯。那时候我在《创世纪》诗刊有一个专栏,专门介绍那些作家,很危险,但是那时候年轻,也不怕。现在台湾熟知的一些作家,都跟我有关系。
南方都市报:比如说呢?
痖弦:比如说王辛笛,是我介绍的,王辛笛后来跟我通信,很高兴。那时候资料不多,都说错了,以为王辛笛死了。后来我到上海,看到他。比如说卞之琳、废名、艾青,这个专栏写了很多年。一开始觉得艾青好,后来就觉得卞之琳比艾青深刻,后来就慢慢发现了穆旦,非常好。
南方都市报:50年代在台湾涌现了很多新诗流派,彼此的争论激烈吗?
痖弦:争论在新诗当中还不是很严重,争论的倒是一批保守的人。画传统国画的人跟画抽象画的人争论,写旧诗的人跟写新诗的人争论,有好几次论战。新诗内部也有一点争论,是纪弦先生跟覃子豪先生的争论,因为他们都是留日的,纪弦先生说新诗要继承西方的从波德莱尔以降的传统,就是“横的移植”,覃子豪先生觉得“横的移植”固然重要,但是“纵的继承”最重要。
其实这两个老先生对我们都有影响。尤其是覃先生,他办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,我参加这个学校,覃先生每一次请我们去吃很好的馆子,我们那时候是穷光蛋,就跟着他。他自奉甚俭,有时候写了一首诗,就在自己吃的担担面里加一个卤蛋,表示对自己的奖赏。(笑)他抽烟太厉害,后来得了病,我们轮班去看守他,像儿子一样,大小便都管。他快去世的时候,叫了很多人的名字,差不多人来齐了才断气。很了不起,是个教育家!他去世后,我们帮他办后事,有一个人姓柴,在灵堂披麻戴孝,执孝子之礼,记者问:“你是不是覃先生的儿子?”他说:“不是。”“是不是亲戚?”“不是,是他的学生而已。”要说文学伦理达到最高点,都是很自然的,不是造作的。覃先生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,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有没有写诗?要写噢,有前途!”(大笑)我们每个人都有他亲笔写的信、改的作品。
南方都市报:当时有好几个著名的诗刊,彼此交流多吧?
痖弦:很多诗刊上写的人都是重叠的,像余光中、郑愁予,彼此的界限分得不是很严格。几个诗刊好像几家院子一样,跑来跑去的。那时候文艺界是不分本省、外省的,后来才分,现在分得很厉害,我很厌恶这种分法,没有意思。文学连国界都没有了,你来一个省界,太可笑了!
南方都市报:60年代中期你怎么开始不写诗了?
痖弦:我的兴趣转了,开始进入杂志界。我把杂志编辑的意义提升到完全是事业的立场。完全是没有休息的时间,越深入就对自己的东西越荒废,但是我对这种荒废是无怨无悔。广义地说,我觉得我编的东西就是我的作品。
在美国做四十几岁的老学生
1966年9月,痖弦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室研习二年。回台湾后,1969年任《幼狮文艺》主编,带起文艺风气,培养了林怀民、蒋勋等人。1976年9月,痖弦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研究所深造。
南方都市报:在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室主要做什么?
痖弦:爱荷华请很多作家到那儿交朋友、讨论作品、参观、访问、朗诵,基本上不是学生,我是第一个去的。聂华苓也是被请去的,后来她跟安格尔恋爱结婚了。后来两岸三地那么多作家都去,跟聂华苓有关系。
南方都市报:到美国时,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见闻?
痖弦:我看到了美国在二战胜利以后的那种强势,那时候越战还没有开始,东西很便宜,民心士气很高涨,我看到了一个尾巴。等到越战一出来,嬉皮一出来,就是满头疱了。我刚去的时候,嬉皮刚刚抬头,等到1968年,他们把图书馆给烧掉了。嬉皮和反越战搅和在一起,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。
南方都市报:嬉皮运动对当时美国文化影响大吗?
痖弦:嬉皮运动对人类的影响蛮大的。从前很多学校的学生要穿得整整齐齐才能上课,整个民间穿衣服是很考究的,衣服变成仪式的一部分。嬉皮一闹,大家觉得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?混碗饭吃就够了,享受人生啊,穿得随便也可以的,现在没有一个大饭店说:没有打领带不让进的。这就是嬉皮运动争取到的,工作的观念,休闲的观念,实现了自由。是好是坏我不知道。
南方都市报:在美国时,知道“文化大革命”吗?
痖弦:知道,那时候蛮轰动的。一开始不了解,一听说“红卫兵”就很过瘾,后来就觉得中国发疯了。
南方都市报:从美国回来后去编《幼狮文艺》,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?
痖弦:这是一个青年刊物,很多作家都是由《幼狮文艺》培养,后来成为很重要的作家。
南方都市报:比如说呢?
痖弦:比如说林怀民、蒋勋。林怀民那时候是高中生,写短篇小说,他写金门:“尸白的沙滩”,就把它改成“苍白的沙滩”,他又把它改回来。(笑)我们两个做游戏。
南方都市报:林怀民原来不是搞舞蹈的?
痖弦:他原来写小说,后来爱荷华的英文系主任到台湾来观光,聂华苓就讲:“好好招待他。”因为爱荷华国际作家工作室是英文系的一个写作计划,彼此的合作很重要。那时候我在编《幼狮文艺》,夏天很忙,我把钱给林怀民:“你去招待这个老先生。”林怀民就陪着他们去玩,这老先生就看上林怀民是个才子,后来邀请林怀民到他们的英文系念书,后来他就开始在那儿跳舞。后来他放弃小说的写作,全面来编舞,创立《云门舞集》,现在差不多国际上的大奖都得了,影响非常大。我到台北,他和蒋勋一定要请我吃饭,照相的时候他们就站在我后面,我像孙中山,他们像蒋介石。(大笑)
南方都市报:大陆现在也出了很多蒋勋的书。
痖弦:蒋勋写各类型的文章,能写诗,能写艺术评论,也写美学的书,也能画画。蒋勋的第一首诗是我帮他发表的。他讲话也很迷人,声音很好听。
南方都市报:后来你怎么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硕士?
痖弦:1976年,去爱荷华的时候“文革”开始,这次去时“文革”结束。“文革”伤中国伤得蛮厉害的。我在爱荷华的时候,一方面当访问作家,一方面选课,在那儿念的学分,拿到威斯康辛去,那学分可以保留十年,十年以后再不学的话,那学分没有用了。我去了一年就拿了硕士。
南方都市报:我记得周策纵先生是在威斯康辛大学。
痖弦:对,周策纵是我老师。周先生考据义理都非常好。他除了研究五四运动史,做很多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考据,还有文字学。他是很渊博的学者,教我治学的方法。我问一个字,他能讲一个小时。你在走廊上问他一句,他就站在走廊上讲一个小时,你又不好意思走,因为是你问的嘛。(大笑)他的生活非常简单。那时候刘绍铭也在那儿教书。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几岁了,老学生。
报纸的个性展示在副刊里
1977年10月,痖弦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学位。同月,应《联合报》之邀,出任联合副刊主编。1980年升任《联合报》副总编辑,仍兼副刊组主任。1984年,痖弦创办《联合文学》杂志,任社长兼总编辑。1997年1月,举办“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术研讨会”,提出“副刊学”的构想。1998年5月,获“第一届五四奖·文学编辑奖”。是年8月,从《联合报》退休。
南方都市报:你到《联合报》副刊时,那是报纸副刊辉煌的年代?
痖弦:那时候不仅是联合报副刊辉煌,其他的报纸也都是发热发光的年代。所有编副刊的都是很认真的,那时候副刊登一篇文章的话,那就是家喻户晓,满街的人都在看。因为那时候在新闻方面管制得比较严格,大家新闻都差不多。假如一个总编辑要任用,总是党部要通过。有一些事做得出格的话,过一阵这个总编辑就会下台,表面上看跟官方没有关系,实际上都有关系的。副刊因为是能用文学这种感性的形式,还能表达一点抗议,所以跟官方意识形态不太一样的东西都在副刊上出现了。在副刊还可以得到一点舒解,一点发泄。所以副刊变得很重要,知识分子、个人主义者的意见甚至对大陆肯定的东西,都在副刊上出现了。副刊就变成比较广义的激进的带点左派色彩的管道,做政府的诤友,争取民主,有反抗的意识。在禁忌的时代,也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出来。有些文章在副刊出现的时候,就不会用严格的尺度来衡量。
我一直认为,一个文人应该是一个“广义的左派”。所谓“广义的左派”,就是永远对政府采取一种监视和批判的态度,因为政府有它的政府机器,有宣传的队伍,有笔杆子队伍,有写作班子,用不着文人在它香炉里再加一炉香。所以这个时候文人就要做一个“广义的左派”,站在土地、人民、大众的立场说话。比如你原来支持陈水扁,当陈水扁变成执政党的时候,你就要调整自己的角色,再不能变成他的“粉丝”了,否则就糟糕了。如果你做一个“狭义的左派”的话,你可能就会陷入党团的利益里边,党团都是经常有变化的,党团是排外的,甚至党团是黑暗的也说不定。
南方都市报:在编《联合报》副刊时,政治上的压力还大吗?
痖弦: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等到伤痕文学出现前后时,我已经大量地邀约大陆的作家给我写东西了,像沈从文、萧乾、施蛰存、赵清阁、卞之琳、白桦都写过东西。没有人教我怎么做,我自己就很自由。那时候台湾的稿费高,大家都来了,有的人主动跟我联系的,有的是我自己约的。大陆的作家多嘛,我就尽量地登,登到台湾的作家都不高兴了,骂我说:“你们这个报纸毕竟是为哪办的?怎么那么多大陆的作家?”后来我还创办了《联合文学》。我曾经送稿费到沈从文家里去,沈先生有一幅字送给我。施蛰存跟我通信,有一封信我要找出来,他言下对鲁迅不满意,觉得鲁迅有点暴得虚名,他的意思是:鲁迅是不错,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吧。两岸的文学交流,我可能是最热心的一个人。
南方都市报:当时《联合报》有没有定下一些办报的理念?
痖弦:没有,我的老板告诉我一句话:“国家的利益高于报纸的利益。”要正派办报,不要为了多销几份报纸就胡来。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:“人无我有,人有我好。”
南方都市报:听说当时《联合报》副刊培养了很多新人,是一个重要的阵地。
痖弦:《联合报》有一个小说奖,那是培养作家、发现作家很好的方式。台湾的小说奖,奖金多,公正,绝对不会说有“内定”这些事情,而且评审的意见全文都登出来了。我请五个人来评奖,我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能讲的。没有人敢兑一点假,那时候得一个奖真是一种荣耀。参奖的人很多,每年是盛事,很多人得了那个奖,比如朱天心、张大春。我们帮助过很多人,我们希望副刊不但是文字的,也是动态的副刊,所以大的学术会议也开,好像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副刊所能负荷的。你自己强烈的个性展示在你的副刊里。那时候报纸也赚钱,所以我出版过《联合报》三十年文学大系,比新文学大系的量还大。
南方都市报:当时《联合报》和《中国时报》竞争厉害吗?
痖弦:因为两份报纸都是发行一百多万份嘛,所以竞争很厉害。《联合报》副刊是我责编,《中国时报》副刊是高信疆责编。高信疆善于进攻,我善于防御,所以也各有得失。后来大家都拿来说笑话,因为高信疆是新闻系毕业的,我开玩笑说他有“新闻记者的劣根性”,喜欢抢时间,副刊本来是不抢时间。比如诺贝尔文学奖,8点钟宣布一个名字,第二天就是一个整版,有时候非洲一个地方的人得奖,你不知道,所以要准备一年,世界有多少重要的人都有准备档案,请郑树森帮我们设计,很多人他都认识。我们就像抢体育新闻一样抢文学新闻,而且我们的新闻报道都超过西方媒体,慢慢地也刺激了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会,每年我们都问他们:“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得奖,你们对我们的文坛知道多少?”
南方都市报:马家辉在一篇文章里说,张爱玲住在美国时,你曾派女记者去访问,女记者偷翻张爱玲的垃圾,这可能是第一代华人狗仔队。文章写成后,你认为不合情义,拒绝刊登。记者忿然把稿子投给竞争对手《中国时报》的人间副刊,那边也是拒登。
痖弦:这个事情我已经跟马家辉讲了,不是我派的记者,是一位小姐,她是我们学生辈的,她住在美国,打一个电话给我,说:“我准备访问张爱玲,如果访到了,这个文章你有没有兴趣?”通常我们接到这样的电话会说:“可以呀,你寄来嘛。”这跟我派她是不一样的。再也没有想到她去扒人家垃圾,扒人家垃圾是太严重了,这是犯法的嘛。她就把每天扒到的垃圾作分析,很无聊的。所以当时她把文章交来,我没有登,她很快拿到《中国时报》去,也没有登。
南方都市报:马家辉是有感而发,现在香港的狗仔队就是每天到明星楼下扒垃圾,分析一下就写文章了。
痖弦:这个事情你要帮我公开,这样有伤我的清誉。张爱玲很少跟人写信的,她是不回信,不接电话,也不应门,你要访问她是很困难的,人人都知道,不必访问。她在台湾跟我有来往,写信给我,我常常接到她的信,我知道不必去访她,访也访不到。她不要见面,我也没有见过她的面。我不会幼稚到去访,也不会去扒她的垃圾,那是非常龌龃的行为。
南方都市报:沈君山的《浮生再记》的后记写得很好玩,讲到张大千去世的前一天晚上,他正好和《联合报》总编辑张作锦在总编辑室闲聊,看到副刊为了等张大千去世的消息,准备了悼念张大千的版面,如临大敌的情景。
痖弦:他带点嘲笑的口吻,说版做好了等着那人死。版做好了,是超过80岁的人资料我们都有。世界上的大报都是这么做的,重要的人如果一过世,一定要报道的。我们叫“松柏长青”档案,“松柏长青”还是有祝福的意味,不是说80岁以后将来死掉了我们都要用,多难听啊。但是,到了80岁以上,我们都建档的。万一他过世,每报都要抢新闻,资料都在。不是说版做好了去等他死,他不死还觉得很遗憾。沈君山常常在我们编辑部说俏皮话,我想他没有什么恶意。
南方都市报:我听说你给人家写了40万字的序,是怎么回事?
痖弦:对,因为他们的文章都是我编,觉得我熟悉,就让我写序。序言后来在台湾,已经变成人家不尊重的东西,认为是人情文章。后来我就想,我们中国的唐宋八大家,那些序写得多好呀,序言是很正式的作品,而且不是副产品,都是主产品。我答应人家写序,就把它写好。我一篇一篇地写,写了就放在那里,后来整理了以后,有40万字,我是把它当正式作品来看。
南方都市报:你曾经在“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术研讨会”上提出“副刊学”这个概念?
痖弦:我把副刊提高到学问的层次,所以有很多硕士、博士论文都写副刊。我在退休之前,把心愿表达出来。因为中国报纸和西方报纸不同,西方报纸没有的就是我们的副刊。体例最完备,每天都有,而且跟我们的文坛息息相关的,所有的青年作家都是在这上面培养出来的。这么重要的东西,是我们文学发展的命脉之所在,也是把文学送到每家信箱的一个作为。
采写/摄影:本报记者李怀宇
本栏目精华已结集成系列丛书,第一辑《最后的文化贵族》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。邮购热线:020-87373998-8502;地址: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出版社发行部。